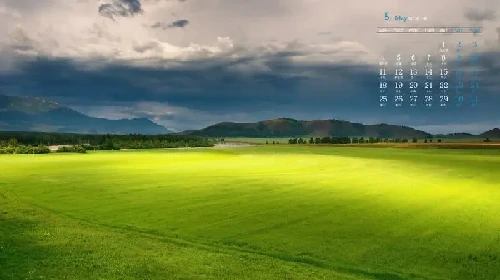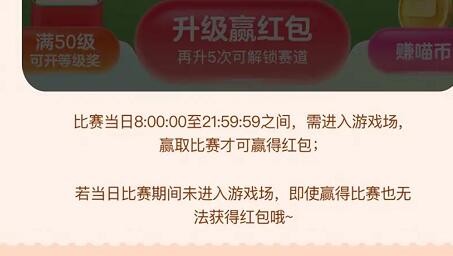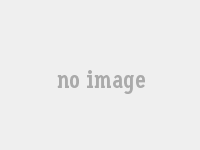这题出自哪本书长什么样,去哪里可以买
淘宝搜:【红包到手500】领超级红包,京东搜:【红包到手500】
淘宝互助,淘宝双11微信互助群关注公众号 【淘姐妹】
摘要 亲,【中学数学新课标】网上有卖的哦,新华书店也有哦!新华书店是中国国有图书发行企业,1937年4月24日成立于延安清凉山,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,中国出版集团之下,是国家官方的书店,也是国家刊物宣传与发售处之一,新华书店总店不同时期曾直属于中央党报委员会、中央出版委员会、中央出版局、中央宣传部、国家出版总署、文化部、国家出版局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领导机关。亲,有其它相关问题咨询的话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哦!
那些年那些事主题曲
转自:邯郸日报
王富河
我1984年元月担任涉县团县委书记,进入涉县县委大院,2003年8月在涉县县委副书记任上,调市委政法委工作。其间,除在担任涉县纪委副书记时,1992年到固新镇挂职党委书记不足一年外,在涉县县委机关工作长达二十年时间。
虽时过境迁,然而,当年县委机关干部、职工的工作、生活、精神风貌、工作作风及人际关系等,至今仍然历历在目,记忆犹新,每念及此,仍感温馨。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,那些年,发生的那些事,我总想用文字记录下来。
伙房门前小石桌
1983年底以前,涉县县委、人大、政府及政协,包括县委各部门、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部门,同在城西街中段路东(现涉县第四中学对面)的一个大院内办公,也称“县委会大院”。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,机构的扩大,原大院的办公用房日趋紧张,1982年又在路对面的第二招待所院内建一栋新楼(现涉县第四中学),1983年底县委及各部门搬入新楼办公。我到团委任职时,县委刚搬入新址。
县委搬入新址后,机关伙房必不可少。当时机关干部大多为“一头沉”,就是本人在单位上班,家属子女为农业户口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。紧临县委北侧为印刷厂,靠近县委围墙有印刷厂几间仓库,经与之协商,腾出两间仓库,一间盘上灶台,支起案板就是厨房操作间,另一间房顶拉上纱布以防灰尘掉落就是餐厅。其实餐厅既没有餐桌,又容纳不了几个人,主要是一个排队买饭的地方,院子里有几块用砖支起的水泥板,就是吃饭的餐桌。县委机关干部和印刷厂工人共用一个伙房。领导干部没有专用小食堂,县委书记和机关干部职工、印刷厂工人一样,也得站在那里排队买饭,都是一样的饭菜,也不会少掏一分钱。有时候大师傅看到书记排在后边,示意递过去碗先盛,也会被书记婉言谢绝。原县委书记武永昌的老伴家住在曲周农村,农闲时偶尔来小住几天,都是来时在老家带点小米,早晚在食堂买两个馒头,买几分钱的咸菜,用小电炉在办公室熬点米粥,老两口坐在一起,吃得津津有味。
接替武永昌担任县委书记的是程鸿飞,从省直机关工委调来,是部队转业干部,工资较高,家里生活条件较好。而机关食堂每天早、晚都是馒头、窝头、玉米面糊糊加咸菜,中午是、面条加土豆、白菜熬的大锅菜,程书记刚来时不习惯,就另外交钱让大师傅炒个鸡蛋。在大家看来,这已经十分奢侈,尽管自己出钱吃得好点,印刷厂的工人还是在背后议论书记有钱生活特殊。听到议论后,程书记决然改变生活习惯,一起排队买饭,吃一个标准的饭菜。
开饭了,去得早点儿的人,可围坐在水泥板餐桌周围,去得晚了,只能在院内靠墙蹲下。大家边吃边聊,天南海北,东拉西扯,大到国家大事,小到鸡毛蒜皮,奇闻轶事,无所不及,神吹瞎侃。一顿饭下来,一般都在个把小时。有的不午休,还要摆上象棋厮杀几盘。
“衙门”面向百姓开
县委大门口设有门卫,也叫传达室,由两位退休老人值守,主要职责是早上开门,晚上关门,打扫大门内外卫生,收发报纸信件。平时更多的是为老百姓办事提供咨询,比如,告诉来访者哪个单位办公室在几楼之类,没有阻止老百姓入内和拦截上访的职责。
老百姓到县委反映问题,县委领导的办公室都可以推门就进。机关干部见领导,更没有预约、经秘书同意的程序。
当时,干群关系和谐,大家不太关注领导,只是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。领导平易近人,出行与平常人无异。有时候,领导在楼上忙累了,想活动活动筋骨,就下楼来和同志们聊聊天。晚饭后和同事们下下象棋。
团县委、县科协两个单位为一个党支部。一次,组织党员学习,人还未到齐时,几个人在聊天,突然电话铃响起,科协副主席张凤英拿起电话,“喂,你找谁?”电话那头说:“我是武永昌,刚才一个人来办公室卖菜籽,你们帮助他统一联系一下,别让他各个办公室乱跑,影响大家办公。”张凤英赶紧回答:“好的,武书记。”刚放电话,本单位李宪禄同志走进办公室,一脸不高兴地说,“咱们从农科院联系到一种优种萝卜籽,我去二楼,到一个办公室有个老头,我一片好心看他要不要,他倒说不要到各个办公室乱跑,影响机关办公,真是不知道好歹。”张凤英问,你不知道那是谁吗?李宪禄说反正是咱们县委机关的,上下楼经常碰到。凤英说,“那是武永昌书记呀!”李宪禄说:“他就是武书记呵。”
程鸿飞担任涉县县委书记时,一次从办公室出来,准备下乡调研,在办公楼前恰遇上访老户王小三。王小三向书记反映问题,程书记看其一时也说不清楚,就与他商量换个时间再说,小三说,我来一次不容易,来了也不见得能碰上你,还是今天谈吧。程书记一听也是,索性推掉其它公务活动,转身进县委办公室取来两张旧报纸,递给小三一张,两个人把报纸铺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坐下,头碰头,面对面,小三从自己年轻时因大哥结婚,嫂子要的财礼太多,导致英俊潇洒、一表人才的自己没钱娶媳妇,而断子绝孙,一直到大跃进时因自己不愿参加劳动,公社办“学好班”让自己劳动半个月没给报酬。整整三个小时,王小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才说到1960年。程书记听得认真,问得仔细。不了解情况的人,还以为这两位是久别重逢的老友,在促膝交谈。
县委书记的小公交
1980年我在合漳公社当农业技术员,与管委主任师德贵一块分包白芟村,这也是县革委副主任杜二山的联系点,他来村蹲点调研大多是乘坐公交客车,很少有小车接送。他和我们一样,经常住在村里,在老百姓家里吃派饭,一天交三毛钱一斤二两粮票,白天下地参加劳动,晚上同我们一起睡在原来是个大庙的大队部的土炕上。
那个时候,从县城到西达是标准不算高的柏油路,而西达到合漳是简易公路,客车能勉强通行,但弯多、弯急、坑凹不平。有人数过,仅台庄至黄龙口就有132个弯。晴天客车通过尘土遮天蔽日,下点小雨,便道路泥泞,不能通行。所以通往合漳的客车很不规律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天上只要有点乌云,客车只到西达就不敢继续前行,不然一旦有雨,车就会陷在泥里,毫无办法。我老家是龙虎公社王家庄大队,每次回家,只能利用每月8日到县农业局开例会的机会,顺便拐拐,单程整整一天时间。去时从县城坐通往邯郸的客车到鸡鸣铺,步行15华里到家。返回时步行20华里到西戌坐客车到县城,因为鸡鸣铺不是车站,下车没有问题,上车就很不靠谱,客车来了是否停车,那就要看车上人多人少和司机的心情了。
1982年我在河南店公社会里村蹲点包村。麦收时节的一天,县人大常委会老主任张学书一人拄着拐杖,头顶炎炎烈日,步行到了村里,了解三夏进展情况。我说张主任这么远的路程,你也不让小车来送你一下?张主任说,我现在不是太忙,步行走走,看得多,听得多,更便于了解情况,他们年轻人(指县委、县政府领导)事多,车尽量让他们用吧!
1989年河北日报曾经有一个报道,题目是《县委书记和他的小公交》,讲的是涉县县委书记程鸿飞乘车下乡途中,遇到步行的老乡都要捎上一程,尤其是对老弱病残更是格外关照。如果他没有急事都会绕道送送,所以每次出行车上都是满员。
改革开放之初,涉县有一项政策,知识分子家属可以“农转非”。孔祥江同志学校毕业后回原籍魏县一所学校任教,为了解决家属和子女的户口和就业问题,主动报名到涉县工作,安排在县委宣传部。一次到邯郸开会,返回时在汽车站坐上客车,正好一位同学从车前路过,孔告诉同学已调涉县县委工作了。车开后,坐在他身后一位身穿带有油污军大衣的中年男子,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,你在县委哪个部门?孔十分惬意地答道:县委宣传部。“我也在涉县县委工作,你认识我不?”孔祥江认真端详了一下,有点面熟,在大院经常见,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,毕竟才来两个多月。看穿的衣服像食堂大师傅,但在食堂吃饭,三个大师傅已经熟悉了。再看,也不是小车司机,县委机关只有两辆小车,两个司机在院里经常见,也不是。他脱口而出:“烧锅炉的?”对方摇头。“修理工?”对方又摇头。孔祥江想:也不是电工,电工老赵我们两个偶尔还下盘棋,那这个人是干什么的?对方看他实在想不起来就问:“你知道不知道葛双庆?”孔祥江恍然大悟,“哎呀,葛书记!”(县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),顿时面红耳赤,羞愧难当,他怎么也想不到县委副书记来邯郸开会也和自己一样坐客车,而且看穿着怎么也像是锅炉工或大师傅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整个县委大院只有一辆北京吉普,后来增添一辆三菱面包,承担着县委领导和县委各部门公务活动用车的主要任务。但小车在车库闲置的时间很多,县委各部门,甚至各常委没有特殊情况很少用车。县内活动除少数几个公社通公共汽车,大家坐公交出行之外,其余多以步行或自行车为主。
春节前是两辆小车最忙的时期。机关的大部分同志都可以享受一次坐小车回家过年的待遇。大家几个人一路,连人带置办的年货塞得满满当当,一路颠簸,虽然挤得不舒服,但心里却溢满幸福。
人民公仆高喜顺
高喜顺,1928年生于偏城镇小交村一个农民家庭。从小身患残疾,历经艰辛与磨难。12岁参加农会,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。领导青年开展抗日斗争,积极参加土地改革,敢于斗争,不怕牺牲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长期担任县委领导职务,并曾代理县委书记。他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一心为民,荣辱不惊,靠着一双残腿,凭着顽强毅力,跑遍了涉县的山山水水,哪里艰苦就到哪里,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肩背粪筐(路上看见牲畜粪便都要捡起倒进田里)是他出行的标配。关于高书记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、扶危济困、一心为民的很多故事在涉县广泛流传,在老百姓心目中,高喜顺就是党的化身,神一样的存在。直至后来每当我看到“一心为公”“人民公仆”的字眼,在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老书记高喜顺的形象。
原西达公社党委书记陈文华回忆,1963年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,清漳河流域受灾尤其严重,交通、通讯瘫痪,乡、村都成了孤岛,一天高书记拄着木棍,翻山越岭满身泥水一瘸一拐到了西达,察看灾情,慰问受灾群众,指导抢险救灾。干部群众看到高书记到来,眼含热泪,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看到了家长,在孤立无援中找到了依靠,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,坚定了大家战胜困难信心和决心。很难想象那时既无涉林公路,更没有西达大桥,高书记拖着残腿,不知走的哪条道,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西达的。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只身赶往合漳和太仓。
1982年秋,我还在农业局工作,局长安排我陪时任县委副书记高喜顺下乡调研、督导秋收种麦进展情况。我和农机局一位技术人员,还有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,与高书记同乘一辆吉普车到马压社。在公社书记崔伏虎陪同下,不仅深入到村,而且到田间地头,实地察看,座谈了解情况。返到公社已经中午,崔伏虎说,“出门时已经给你们报饭了,就在这里吃饭。”高书记问:“中午吃什么饭?”崔答:“书记很长时间没有来了,今天咱们改善一下生活,吃水饺。”高书记一听说吃水饺,立即招呼我们:“咱们回去还有事,赶紧走了。”上车后高书记说,“这是专门给咱们做的水饺,这个便宜不能沾。”如果回县城,机关食堂已过饭点,街上又没有饭店,我们只能饿着肚子。路过偏店公社,高书记说,进去看看还有饭没有?进到院内,机关干部刚吃过午饭,围坐在食堂门口的水泥板餐桌周围,面前放着空碗在聊天。见我们进来都站起来问候,高书记问,食堂还有饭没有?公社书记江天来面有难色,说:“我们刚吃过饭,今天中午吃的面条,锅里可能还剩点碎面条,也泡成糊糊了。”高书记说行,有点就行,就在这里吃饭。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半碗糊糊面条。我们还没放碗,高书记已经去交清了连同司机我们五个人的饭钱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和县委领导直接交往接触。
高书记对国家、对他人、特别是对困难群众慷慨大方,对自己、对家人又异常吝啬。文革中受到迫害,恢复工作后补发的工资他全部交了党费,邢台地震、唐山地震、汶川地震、涉县洪灾、南方水灾他都倾其所有,毫不保留积极捐款,帮助过的困难群众更是不计其数。但自己吃的是糠糠菜菜、粗茶淡饭,穿的一身衣服穿了又穿,补丁摞补丁。他自己是离休干部,医药费全部报销,但老伴大灾小病就是五毛钱药片也必须自己付钱去买,绝对不沾公家一分钱便宜。